本书从符号学的视角观照经典注释和中国典籍文化的发生发展历程,将经典注释的基本精神和中国典籍文化的基本内核界定为多层级的“二元互补”结构,把中国文化史上针对这种深层结构进行的不断地文化阐释定义为“原解释”。在中国典籍文化中,神话的结构规则及其针对这个神话规则的阐释方式共同规定了该文化的根本意识形态走向和它的基本功能。典籍文化中的“根本意识形态”包含三个层面:即典籍的“结构形态”层面、“表达形态”层面和“应用形态”层面。如果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问题,这三个层面的基本功能主要呈现为符号的遮蔽和投射功能、符号的本位和认证功能、符号的教化功能,并且广泛投射于社会的各个主要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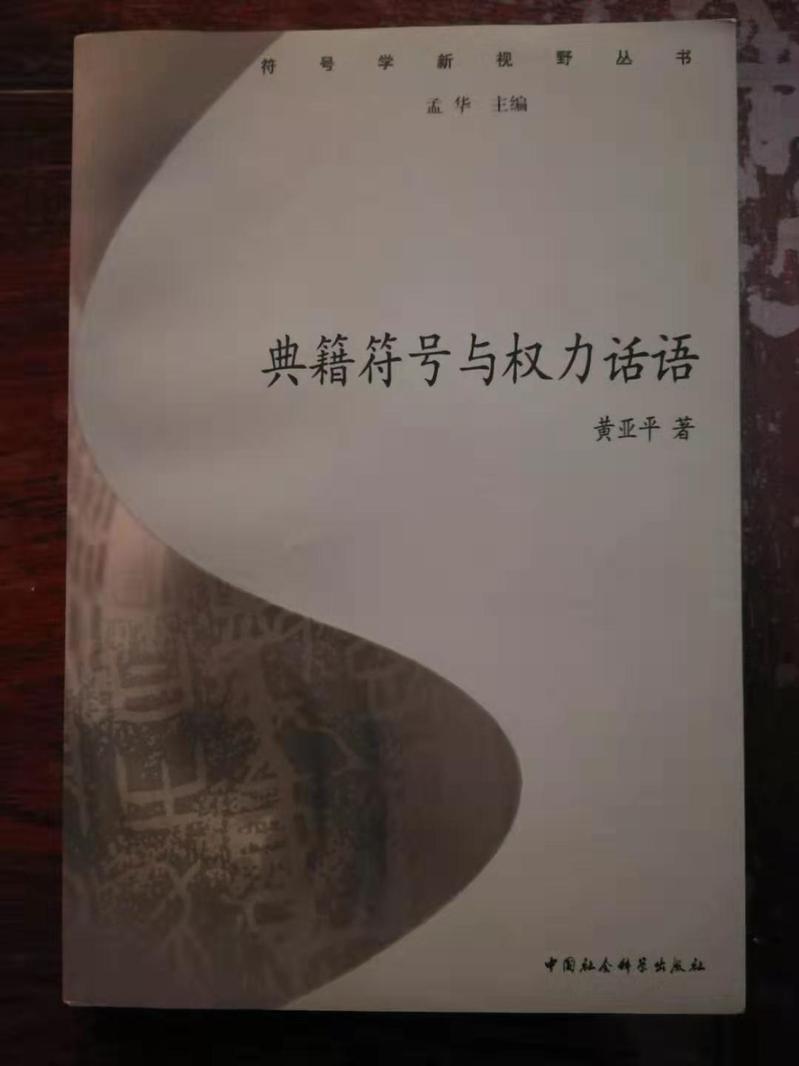
导 言
黄亚平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受了世人,尤其是国人的无情批判。流风所致,不但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受到猛烈的抨击,就是他的末流枝节也一并受到株连。但是,从今日的眼光看,这种对文化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却并没有建立在对这个文化自身地冷静分析和客观评价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激愤和感受的情绪化层面上,更多地是对这个文化的非现代性的忧虑,而不是对这个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尽快实现现代性的思考。
20世纪后半叶,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人们逐渐意识到:政治、经济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但还应看到他们各自的独立性。文化的落后自然可以导致政治、经济的衰退,但古今中外的许多例证也说明,落后的文化也可以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先进的文化。同样,先进的文化也有可能孕育出并不先进的政治、经济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古老的中国文化的振兴也自然而然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文化大脑”的学术界也在普遍地思考着以下的问题:
第一,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融合究竟是不是大势所趋?现存的世界各文化之间到底有无融合的可能?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加以融合,使其统一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系统之中,那么,各不同文化之间能否做到互相尊重,相互包容,互相借鉴?
第二,在世界范围内,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传统以及亚、非、拉的许多文化传统在世界文化中应该各占有什么样的位置?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根本矛盾和冲突在哪里?我们是否能找到既借鉴了外来文化的长处,又较好地保留了中国文化的长处的道路?如何避免两种文化的冲突带来的民族性灾难?
第三,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新时期的中国文化能否跟古老的中国文化一样,长时期的、不断的对外输出些有益的东西?能对人类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样的新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民族性?在什么地方具有世界性?
想要回答以上问题,必先高举文化观照的旗帜,具有超越本民族文化的眼光,并在此背景之下,对本民族文化有一个结构性的深层把握,弄明白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了解这些基本的结构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各主要方面的渗透和影响。也就是说有必要先对自己的文化来一个清仓查库式的大盘点,弄明白自己的库存里到底有多少可用的材料,然后才能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和综合研究。
通过与异文化的比较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优劣,不但是当前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振兴所需要坚持的道路,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各文化都应该走的道路。事实上,世界各文化体中的知识分子们从来都没有停息过对自己文化的深刻反省。我们以为,虽然不同的文化体之间,自古以来就存在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只要人类有共存的愿望,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吸纳就是解决冲突实现和平共处的最为理想的归途。
就国内的学术研究思路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跟以前相比已经是非常开放的了。显然21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更应该具备世界的眼光,这是时代给学术界提出的任务。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个任务,所谓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民族进入当代世界民族之林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我们应该沉下心来,进行冷静地、客观地、深入地思考,进行独立地学术研究,充分彰显研究者的学术个性,自觉拒斥学术外因素的影响和干预。
我们这里对典籍符号进行的研究是比较与综合研究的结合。其目的是要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的范围之中加以观照,首先为这个文化设立一个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为参照点,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人类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普遍的关系,通过对关系项的揭示和关系之间的对比,凸显传统的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同时为对立或互补的另一方提供文化生存的空间,以确保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元素的充分展示。要达到我们给自己确定的这样一个目的,显然不能仅仅采用传统的从文献到文献的材料排比整理的方法,而必须同时兼顾各个方面,从活的考古材料出发,结合文献的记载,到人类学方法的借鉴,再到语言学考证方法的使用,试图综合以上各个方面的成果,以充分观照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
要想弄明白一种文化体的深层结构及其文化精神,必先深入哪个文化的神话叙事之中,看看神话的构成和运行规则对文化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化最深层的结构模型是时空混同的二元互补结构,这个结构模型是由史前时代中国大地上东、西两大族团共同建构的并为两大族团的后裔们不断坚持的文化内核;这个时空架构以神性典籍的面貌出现,并成为其后的文化叙事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参见第一章)
虽然说时空混同的二元互补结构及其神性典籍的表达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并成为其后文化叙事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但是,只有神话的规则,并不能确保证这个规则的正常运行和神话规则的延续。在不断变化着的历史条件下,想要确保神话规则的正确方向,还必须借助神话叙事方式的不断重复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自觉传承意识。也就是说,神话虽然叙述神们的故事,但叙述方式却是为人所有的;没有人的持续不断的叙述,就没有神,当然也就不存在神话;人对神话的叙述方式决定了神话规则运作的方式,也决定了这个神话的性质。换句话说,神话及其典籍是天生具有可阐释性的文化母体,正是靠了人对它的不断阐释,神话叙事在人类生活中才具有了永恒的意义。(参见第二章)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时空混同的二元互补结构及其表达形式——神性典籍看成是中国文化的原型符号,那么,针对这个原型符号的不断地阐释和文化延续的观念就是具有原解释性质的中国文化的符号操作规程。或者我们径直可以说,典籍叙事中的四时、五行观念(包括以典籍的形态出现的神话的、半神话的四时、五行观念)主导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势。在中国文化中,典籍既是叙事的主体,又是叙事得以成立的土壤,神话的半神话的四时、五行观念则是这个叙事结构中隐含的原则和表达方式。从这个角度立论,中国文化就可以从整体上称之为“典籍文化”,典籍的叙事以及针对典籍的阐释始终是这个文化最为根本的任务。
在典籍文化中,神话的结构规则及其针对这个神话规则的阐释方式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意识形态,同时也规定了这个文化的基本走向和主要功能。
典籍文化中的“根本意识形态”应该包含三个层面,即“典籍的结构形态”层面,“典籍的表达形态”层面和“典籍的应用形态”层面。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这三个层面的根本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功能则主要呈现为符号的遮蔽和投射功能、符号的本位和认证功能、符号的教化功能。
所谓符号的遮蔽和投射功能比较集中的体现在文字和典籍及其它们的关系上。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典籍”,只是用文字记载的“书籍”的代名词而已。可是,如果我们追溯“典籍”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若着眼于“典籍”的发生,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典籍形成的早期阶段,担当记载功能的“文字”和被记载的“典籍”之间也是界限不清的,“文字”和“典籍”之间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们都是祭祀活动的道具,或者说是阿斯曼所说的“文化记忆”,是神灵祭祀仪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背景下,很显然,典籍的结构形态和文字的结构形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同构性,或者说文字的结构形态对典籍的结构形态影响极大,文字的结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典籍的结构原则。(参见绪论部分和第三章)
我们这里所说的为“文字”和“典籍”共有的结构原则正是哲学家、文艺学家们反复阐述的“隐喻原则”,只不过在我们看来,所谓“隐喻原则”本为文字和典籍所有,其后才进入哲学、美学等理性思维的范畴;而在哲学家们看来,“隐喻原则”本属于哲学范畴,其后为文字学、文献学借用。所谓“隐喻原则”,其实质是在并不实际存在联系的对象之间建立一种貌似存在的关系,并使用强制的手段让人们熟视无睹,信以为真,这是原始思维里普遍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一旦人们在隐喻的喻体和本体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真实的客观联系”就不可能在场,在场的只能是人为的“真实”。而在“隐喻原则”广泛通行的文化中,“真实性”并非人们的真正需要,人们需要的只是维护所谓“真实”的符号表达手段而已,或者说是符号能指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构成方式以及在被动欣赏这种方式的过程中形成的审美观念。
“隐喻原则”凭着自己对符号表达形式的强调很自然地取代了符号的结构形态,它使物体与符号之间本应有的主、客体对应关系走了样,它甚至在符号能指间建立了错综复杂的种种联系,使人们在惊异于符号能指的无穷变幻中丧失了对符号所指意义的兴趣。凭借着礼乐文化传统的一次次复兴和重建,“隐喻原则”在历史阶段依然维持着它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的伦理哲学及其这种哲学得以建立的基石——礼乐文化传统都为“隐喻原则”的存在和继续发挥作用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五行生克制化”的政治理论也都处处闪现着隐喻性的比拟。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问题,所谓符号的本位和认证功能主要体现于符号传承过程中传承人以及他们对符号传承所抱的态度上。今天,只要我们一谈到“典籍”,总是很自然的把它与创作个体联系在一起。在现代人的眼中,“典籍”属于人类个体的精神创造,它是从作者个人的头脑中诞生的“孩子”。这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典籍形成的全过程,尤其是当我们把关注的焦点放到发生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时代的“典籍”的创制和它的表达,其实更多是“群体意识”或者是“文化记忆”的产物。而在华夏文明的早期,所谓“群体意识”或者说“文化记忆”实际上是以王官为代表的主流文化意识的代名词。既然王官代表着文化的主流,那么,他们的意识形态当然就是这个文化的本位意识。
本位意识的形成和强化都得益于王官对典籍符号的不断阐释的需要。因为在这个阶段,针对典籍的持续不断地表达的需要而非创新的需求成为文化群体存在的首要任务,更是代表主流文化的精英阶层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正是在对权力原型符号的不断阐释中,王官们成为不但权势显赫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权力话语的持有者。通过对典籍的阐释,他们既笼络了社会的精英,使其紧紧依附在自己的身上,又牢牢控制了话语权,从而成为社会群体中当然的执政者。发展到历史阶段,针对典籍原型的阐释权力又自然转化为“经学态度”。经学态度极大地强化了来自前代的文化延续意识和发展了带有创新意义的学派意识和权力本位意识,成就了历史时代的符号构成规则。(见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第三节)
所谓符号的教化功能是指符号传承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文化延续意识”。在原始的祭祀活动中,针对神灵祭祀的礼乐仪式本身就是该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也就是为原始人所密切关注的生命意义的所在。正象人有延续生命的本能一样,原始的祭祀仪式本身也需要不断延续。延续现时的原始祭祀的最好方式就是把祭祀仪式变成持续的约定,而能够将原始仪式变为持续规程的方式莫过于符号,因此,原始祭祀仪式的固化过程,也就是原始意象的“符号化”过程。而所谓符号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则主要表现为属于视觉和听觉符号的“典籍固化”,也就是用典册的形式将前代的种种礼乐仪式固化为一种可以阅读和解释的礼仪制度,并赋予它代代相沿的唯一性。发展到了经学时代,这种文化传承意识在经学的框架内自然转化为教化的需求。这种内在的教化的需求,经过自孔子以来的历史圣贤的不断强化,最终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重视学习的社会观念。
经过符号化的过程,原始的混沌不分的意象初步实现了主、客体的分离,文明的曙光于是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原始的意象转化为“所指”,意象的表达形式成为“能指”,所指和能指之间产生了“间距”。但是,与断裂的文明体不同的是,连续式的文明体的每一次进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前代原始意象的表达的需要,因此,它所能作出的改变就只能是局部的修正,而不是翻天覆地的革命。综观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从礼俗到礼制,从礼制到礼义,再到伦理哲学,虽然在每一次历史关头,这种文化传承的形式和部分内容都经过必要的置换,甚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中国文化基本意义单位的礼乐形式以及针对礼乐文化传统的文化传承意识却始终永葆青春。真正变化的只是所指内容,能指形式以及针对能指符号的种种偏好并没有改变。(请参第五章)
以上所说的三大原则和三大功能共同承担了历史时代的文化传承意识,留住了这个连续的文化的血脉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的弊端:当它面临外来的文化冲击时候,常常露出种种保守根性,以至于与外来文化不能相容;更有甚者,当这个连续的文明步入以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现代文明时,它遭遇了种种文化的尴尬,面临着重重的困境。以至于有许多人甚至从根本上认为它有可能走到了头,对其能否再一次起死回生表示怀疑。但这已经不是本书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也不是一两本著作就能回答的重大问题了。
